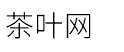探秘滇北鮮為人知的茶馬舊道
發布時間:2025-09-06 點擊:36
末了的茶馬舊道的秘密勾引
世界上再沒有什么門路能像茶馬舊道那樣勾通起無比雄厚的天然和人文的景觀。直到近代,它都是滇川藏地域文化、經濟、宗教融會的重要紐帶。
一樣平常所說的茶馬舊道有兩條,一條是由云南普洱經大理、中甸、德欽等地到西藏,另一條線路是從成都經理塘、巴塘到西藏。這兩條線路是茶馬舊道的干道或動脈。一樣平常的旅游者和考查者,眼光所及都在于此。然而,在彩云之南的怒江江邊,還存在著別的一條最秘密、最原始的茶馬舊道,那便是被稱為“末了的馬幫”的貢山——丙中洛——秋那桶——察瓦隆——察偶的貢察線。
我在茶馬舊道上的重要門路圖中重復查找,找來找去,本來這些所謂的“路”,僅僅是茶馬舊道大動脈上的一條條微細血管。她對我滿盈勾引著,令我不惜用幾個月的時候花兩次精神去細心品味這條舊道。
茶馬舊道上的第二條滇藏公路
說起滇藏路,很多人對214國道并不生疏。因它的滇西北一段和夙昔的馬幫線路非常重合。從云南西去西藏,大師險些都走這條道的。至于怒江大峽谷,在那邊隱蔽著馳名于世的怒江大拐彎。有人說看完大拐彎和體驗過那一帶雄厚的多平易近族的人文氣呼呼息之外,沒有什么值得悅目的了。另有梅里雪山,很多并非宗教徒卻懷著宗教般熱情的同伙在羊年轉過這座神山,幾多也在峽谷里呆過一段時候。
其實,不管是214國道照舊梅里雪山,大概是怒江大峽谷兩側高如云端的碧羅和高黎貢山等等,縱然你走遍了,那其實還遠遠不敷。由于,陪伴著橫斷山走勢的另有一條鮮為人知鮮為人至的馬幫線,這條省級公路范圍的滇藏線從云南貢山直達西藏察隅。它即將被第二條滇藏線所庖代。而它不被山外人正視的程度,就好像這條膝行在將來新公路腳下關閉的馬幫線路一樣,同樣難以被人記起。
隨著第二條滇藏路在此搭建,馬幫終究再難以其范圍雄渾、龍蛇混雜般的遠大撞擊力出現在大天然的面前了。有勇氣呼呼密切大天然的同伙,完全可以在瀏覽完怒江第一彎今后,再往峽谷里更深切細心地閱讀。乃至從214國道進入梅里雪山轉山道,至此直抵西藏昌都或西去察隅。那樣,你大概可以和馬幫一路走在茶馬舊道上,履歷一次他們曾經履歷和如今正在履歷的艱苦里程。那但是現存馬幫文化最真實最雄厚的體驗啊! 馬幫偶而也會穿過較為平坦的叢林。
歷險第一關:
和馬幫一路走過留噴鼻巖塌方區
我的舊道行始于云南貢山丙中洛鄉,至此達到察瓦龍中轉站休整。今后再北去西藏左貢或西去西藏察隅,兩條路給人的印象都鮮活無比。
我的打算是:從青那桶村徒步進入怒江大峽谷,順著本來的馬道走過,然后和馬幫齊集。 領導阿桑說:“馬幫如今就繞到那座山的背后。是以,走這條道大概要一個禮拜,最多10天時候,要看路好不好走。”其實這一段路的艱險連阿桑也沒預計到,末了我們走了21天才走到西藏林芝的下察隅鎮。
隨馬鍋頭央措的日子里,最難忘的歷險是經由過程當地被稱為留噴鼻巖的大塌方區。有一天,我們的騾馬怠倦不堪地行進著,忽然遠遠地看到一個偉大的石灰巖崩塌體高懸于江東岸,形成一個偉大的倒石堆,其頂點橫跨江面一千多米。整座留噴鼻巖的山體呈偉大滑坡狀,留噴鼻巖并不釋放噴鼻味,當地報酬何取這個名字卻不得而知。聽說一年中,難免有人和畜生在經由過程的時辰被擊傷或產生不測。
提起這個處所,周遭相近的老黎民都吐露出談虎色變的神氣。聽說未來的新公路上,當局預備投入大量資金建架兩座橋梁,兩度高出怒江繞過留噴鼻巖這個令人望而卻步的“地府”。想必到當時,山外人可以坐在旅游大巴上,冷眼旁觀般地瀏覽留噴鼻巖的無敵大全景了。
但眼下經由過程這個傷害地帶有兩個措施:要么鄙人午1點之前,趁太陽未把石頭烤松軟之時鼓足勇氣呼呼沖曩昔。假如碰到刮風,只能選擇另一種方式,那便是在江上飛渡,履歷兩次暈眩的溜索才氣跨過塌方區。第一次,我在險些沒有路基的流沙石上面提心吊膽而又警惕翼翼地跑過。第二次,我在江上掛著溜梆飛越,耳邊掠過呼呼的風聲,眼睛直視對岸,基礎不敢瞟一眼江面。待六神無主地度到江對岸,拍拍胸口,發明還在世,才放下心來。但今后,相比于從格布到碧土路段的江上的最淺易的凹形木頭溜梆單手飛越,這里用掛在鋼絲上的溜梆過渡,平安系數已大為增長,算來也是小巫見大巫了。
歷險第二關:
走過浪漫神奇的馬幫路
無論從察瓦龍直達左貢或西去察隅,都是值得選擇的極具魅力且富有挑釁性的門路。假如可以或許追隨馬幫或當地村平易近一路走完這段旅程,除了可以或許時候體驗山川之美和人生之痛之外,你會在與當地人的配合行走中找到無限的興趣。
起首,從察瓦龍鄉北去左貢有兩個選擇。一條蜿蜒的山路順著怒江邊沿逆行而上,路在格日村棄怒江轉向另一條山路末了達到覺麥鄉;另一條線路從察瓦龍到格布經碧土和覺麥,末了達到扎玉直至昌都左貢。后者由于某些路段并不寄托在江邊,以是必須翻越多處山嶺。偶然在大山大嶺中走上一兩天也見不著人影并不新鮮。令人沖動的是,當我碰到講名譽重義氣呼呼的馬幫的時辰,他們城市當仁不讓地接過你肩上的背包,并馬上結為同伙。
明孔村村長旺堆的父親扎那大叔曩昔在互助社里趕馬四十載。我們在西去察隅的路上相伴而行。由橫斷山脈向西一起曩昔,要翻過無數座海拔四五千米以上的大山埡口。 馬幫走在險要的山間
扎那大叔說從察瓦龍西去下察隅要翻大小不等的五座雪山。這讓我心頭悄悄為之一震。于是,我在加瑪拉山口不敢有涓滴的怠慢,來不及喘口吻,就徑直往山下倉促驅馳。其時真有臨時進天國,臨時被卷進地獄的感受;在翻越另一座陰冷的諾日娜山口時,迫于空前的嚴寒,我想出了一個好措施,用馬鬃被雨水打濕的蒸汽給身材取暖。
我們偶然在石洞里熬過一夜,偶然在溪邊的平地露宿。可是碰到下雨的日子就憂傷了。雨水從人字形的膠布往被子里灌,一夜過來,就這么迷含糊糊捱到天亮。可是,馬幫們持久在田野跋山涉水的保存體例,付與了他們浪漫而傳奇的色彩。走到那邊,都能坦然面對。無論刮風下雨照舊艷陽高照,唱不完的歌謠和太陽般輝煌光耀的笑貌始終展示在我們迢遙的路途中。
在這段險些一年中不是下雨便是大雪封山的路途中跋涉,察瓦龍鄉的鄉長說比打第二次世界大戰還費力。聽說當地鄉干部恐于門路費力,一年只到縣上領取兩次人為。末了,我和馬隊照舊馬一直蹄地走了一個多星期,才達到西藏下察隅。
站鄙人察隅這塊濕潤的地皮上,不知道為何,傳統和當代的力量讓我痛楚地抵牾著。一種來不及咀嚼的忙亂和愉快徜徉在我的腦際,稠濁在我一個多月來走過的如夢似幻的路程中。河流的嗚咽聲,老奶奶的白發,不長草的化山,山頂的積雪,另有馬幫遠去的背影……
世界上再沒有什么門路能像茶馬舊道那樣勾通起無比雄厚的天然和人文的景觀。直到近代,它都是滇川藏地域文化、經濟、宗教融會的重要紐帶。
一樣平常所說的茶馬舊道有兩條,一條是由云南普洱經大理、中甸、德欽等地到西藏,另一條線路是從成都經理塘、巴塘到西藏。這兩條線路是茶馬舊道的干道或動脈。一樣平常的旅游者和考查者,眼光所及都在于此。然而,在彩云之南的怒江江邊,還存在著別的一條最秘密、最原始的茶馬舊道,那便是被稱為“末了的馬幫”的貢山——丙中洛——秋那桶——察瓦隆——察偶的貢察線。
我在茶馬舊道上的重要門路圖中重復查找,找來找去,本來這些所謂的“路”,僅僅是茶馬舊道大動脈上的一條條微細血管。她對我滿盈勾引著,令我不惜用幾個月的時候花兩次精神去細心品味這條舊道。
茶馬舊道上的第二條滇藏公路
說起滇藏路,很多人對214國道并不生疏。因它的滇西北一段和夙昔的馬幫線路非常重合。從云南西去西藏,大師險些都走這條道的。至于怒江大峽谷,在那邊隱蔽著馳名于世的怒江大拐彎。有人說看完大拐彎和體驗過那一帶雄厚的多平易近族的人文氣呼呼息之外,沒有什么值得悅目的了。另有梅里雪山,很多并非宗教徒卻懷著宗教般熱情的同伙在羊年轉過這座神山,幾多也在峽谷里呆過一段時候。
其實,不管是214國道照舊梅里雪山,大概是怒江大峽谷兩側高如云端的碧羅和高黎貢山等等,縱然你走遍了,那其實還遠遠不敷。由于,陪伴著橫斷山走勢的另有一條鮮為人知鮮為人至的馬幫線,這條省級公路范圍的滇藏線從云南貢山直達西藏察隅。它即將被第二條滇藏線所庖代。而它不被山外人正視的程度,就好像這條膝行在將來新公路腳下關閉的馬幫線路一樣,同樣難以被人記起。
隨著第二條滇藏路在此搭建,馬幫終究再難以其范圍雄渾、龍蛇混雜般的遠大撞擊力出現在大天然的面前了。有勇氣呼呼密切大天然的同伙,完全可以在瀏覽完怒江第一彎今后,再往峽谷里更深切細心地閱讀。乃至從214國道進入梅里雪山轉山道,至此直抵西藏昌都或西去察隅。那樣,你大概可以和馬幫一路走在茶馬舊道上,履歷一次他們曾經履歷和如今正在履歷的艱苦里程。那但是現存馬幫文化最真實最雄厚的體驗啊! 馬幫偶而也會穿過較為平坦的叢林。
歷險第一關:
和馬幫一路走過留噴鼻巖塌方區
我的舊道行始于云南貢山丙中洛鄉,至此達到察瓦龍中轉站休整。今后再北去西藏左貢或西去西藏察隅,兩條路給人的印象都鮮活無比。
我的打算是:從青那桶村徒步進入怒江大峽谷,順著本來的馬道走過,然后和馬幫齊集。 領導阿桑說:“馬幫如今就繞到那座山的背后。是以,走這條道大概要一個禮拜,最多10天時候,要看路好不好走。”其實這一段路的艱險連阿桑也沒預計到,末了我們走了21天才走到西藏林芝的下察隅鎮。
隨馬鍋頭央措的日子里,最難忘的歷險是經由過程當地被稱為留噴鼻巖的大塌方區。有一天,我們的騾馬怠倦不堪地行進著,忽然遠遠地看到一個偉大的石灰巖崩塌體高懸于江東岸,形成一個偉大的倒石堆,其頂點橫跨江面一千多米。整座留噴鼻巖的山體呈偉大滑坡狀,留噴鼻巖并不釋放噴鼻味,當地報酬何取這個名字卻不得而知。聽說一年中,難免有人和畜生在經由過程的時辰被擊傷或產生不測。
提起這個處所,周遭相近的老黎民都吐露出談虎色變的神氣。聽說未來的新公路上,當局預備投入大量資金建架兩座橋梁,兩度高出怒江繞過留噴鼻巖這個令人望而卻步的“地府”。想必到當時,山外人可以坐在旅游大巴上,冷眼旁觀般地瀏覽留噴鼻巖的無敵大全景了。
但眼下經由過程這個傷害地帶有兩個措施:要么鄙人午1點之前,趁太陽未把石頭烤松軟之時鼓足勇氣呼呼沖曩昔。假如碰到刮風,只能選擇另一種方式,那便是在江上飛渡,履歷兩次暈眩的溜索才氣跨過塌方區。第一次,我在險些沒有路基的流沙石上面提心吊膽而又警惕翼翼地跑過。第二次,我在江上掛著溜梆飛越,耳邊掠過呼呼的風聲,眼睛直視對岸,基礎不敢瞟一眼江面。待六神無主地度到江對岸,拍拍胸口,發明還在世,才放下心來。但今后,相比于從格布到碧土路段的江上的最淺易的凹形木頭溜梆單手飛越,這里用掛在鋼絲上的溜梆過渡,平安系數已大為增長,算來也是小巫見大巫了。
歷險第二關:
走過浪漫神奇的馬幫路
無論從察瓦龍直達左貢或西去察隅,都是值得選擇的極具魅力且富有挑釁性的門路。假如可以或許追隨馬幫或當地村平易近一路走完這段旅程,除了可以或許時候體驗山川之美和人生之痛之外,你會在與當地人的配合行走中找到無限的興趣。
起首,從察瓦龍鄉北去左貢有兩個選擇。一條蜿蜒的山路順著怒江邊沿逆行而上,路在格日村棄怒江轉向另一條山路末了達到覺麥鄉;另一條線路從察瓦龍到格布經碧土和覺麥,末了達到扎玉直至昌都左貢。后者由于某些路段并不寄托在江邊,以是必須翻越多處山嶺。偶然在大山大嶺中走上一兩天也見不著人影并不新鮮。令人沖動的是,當我碰到講名譽重義氣呼呼的馬幫的時辰,他們城市當仁不讓地接過你肩上的背包,并馬上結為同伙。
明孔村村長旺堆的父親扎那大叔曩昔在互助社里趕馬四十載。我們在西去察隅的路上相伴而行。由橫斷山脈向西一起曩昔,要翻過無數座海拔四五千米以上的大山埡口。 馬幫走在險要的山間
扎那大叔說從察瓦龍西去下察隅要翻大小不等的五座雪山。這讓我心頭悄悄為之一震。于是,我在加瑪拉山口不敢有涓滴的怠慢,來不及喘口吻,就徑直往山下倉促驅馳。其時真有臨時進天國,臨時被卷進地獄的感受;在翻越另一座陰冷的諾日娜山口時,迫于空前的嚴寒,我想出了一個好措施,用馬鬃被雨水打濕的蒸汽給身材取暖。
我們偶然在石洞里熬過一夜,偶然在溪邊的平地露宿。可是碰到下雨的日子就憂傷了。雨水從人字形的膠布往被子里灌,一夜過來,就這么迷含糊糊捱到天亮。可是,馬幫們持久在田野跋山涉水的保存體例,付與了他們浪漫而傳奇的色彩。走到那邊,都能坦然面對。無論刮風下雨照舊艷陽高照,唱不完的歌謠和太陽般輝煌光耀的笑貌始終展示在我們迢遙的路途中。
在這段險些一年中不是下雨便是大雪封山的路途中跋涉,察瓦龍鄉的鄉長說比打第二次世界大戰還費力。聽說當地鄉干部恐于門路費力,一年只到縣上領取兩次人為。末了,我和馬隊照舊馬一直蹄地走了一個多星期,才達到西藏下察隅。
站鄙人察隅這塊濕潤的地皮上,不知道為何,傳統和當代的力量讓我痛楚地抵牾著。一種來不及咀嚼的忙亂和愉快徜徉在我的腦際,稠濁在我一個多月來走過的如夢似幻的路程中。河流的嗚咽聲,老奶奶的白發,不長草的化山,山頂的積雪,另有馬幫遠去的背影……